本文目录一览:
- 1、《庭外》“案中案”调查一波三折,夏雨罗晋如何联手破生死危局?
- 2、为什么张良要找樊哙破解鸿门宴危局?
- 3、如何破解现在中国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危局?
- 4、看淡生死,才能不惧生死
- 5、毛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什么意思?
- 6、宋仁宗无子又病得昏迷不醒,大宋危急,宰相文彦博如何破解危局呢?
《庭外》“案中案”调查一波三折,夏雨罗晋如何联手破生死危局?
《庭外》是刚上映的律政悬疑剧,篇幅简短分为落水者和盲区两个单元。这两个单元在相对独立的情况下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案件一开始便从一个九年前的旧案对于一个死刑犯的审核上开展,由于此案疑点重重,又接连牵扯到一系列事情。由演员夏雨饰演的法官,在案件的一开始仅仅16个小时就发生了一系列的事情。被牵扯进一件连环撞击事件让人不禁心生疑惑。
而这部悬疑剧的第一个单元盲区也由此展开。一案牵扯一案,形成了案中案。调查的过程也是曲折。牵连起了无数的令人心生疑惑的案件。由此由夏雨饰演的法官便联系了好友罗晋饰演的律师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希望能够顺利破解。这些案件但是调查的过程却十分不顺利,他们接二连三的进入了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事情。扑朔迷离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剧情令人摸不着头脑,但是在他们两个人的配合下,真相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也会水落石出,渐渐浮出水面。
这两人法官和律师的搭配。组合围绕着多年前的陈年旧案展开一系列的破解,这个案件从盲区开始经过一系列的调查,两人又发现了与之关联的另一个案件,由此落水者也开始浮出水面。两人携手突破重重难关。案件的调查过程十分困难,同时也是生与死的较量。相信他们会突破迷雾,让真相重见天日。
为什么张良要找樊哙破解鸿门宴危局?
鸿门宴,刘邦所带部将被司马迁点出姓名的有樊哙、夏侯婴、靳强和纪信等四人,为什么在“项庄舞剑,意在沛公”的危急关头,张良会赶紧走出宴厅,找樊哙来解鸿门宴之危局呢?
这主要有三个原因:第一,樊哙智勇双全,这从“樊哙闯帐”本身即可看出;第二,樊哙和刘邦的亲密关系,樊哙娶刘邦妻子吕雉之妹吕须为妻,樊哙和刘邦是连襟关系;第三,樊哙和张良的关系非同一般。司马光《资治通鉴》有如下记载:
冬,十月,沛公至霸上;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降,杀之不祥。”乃以属吏。
沛公西入咸阳,诸将皆争走金帛财物之府分之;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府图籍藏之,以此沛公得具知天下厄塞、户口多少、强弱之处。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家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张良曰:“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所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沛公乃还军霸上。
由此可见:沛公还军霸上,虽然是樊哙和张良联袂谏诤的结果,但谏诤话语的原创权,在张良看来,却是属于樊哙的!有人觉得樊哙只是一介武夫而已,他的口才也很一般,“樊哙闯帐”应该不是他临时发挥的一场戏,而是在张良的导演下精心排练出来的。如果我们只是就《鸿门宴》而论“樊哙闯帐”,这种说法似乎不无道理;但把它和《高祖本纪》、《留侯世家》尤其是《樊郦滕灌列传》等连贯起来阅读,却可发现问题所在:劝沛公还军霸上,虽然是樊哙和张良联袂谏诤的结果,但谏诤话语的原创权,在张良看来,却是属于樊哙的——樊哙并不是一个任由张良导演的演员!也因为此,在“如厕密谋”中,刘邦提出“今者出,未辞也,为之奈何?”之时,起谋士作用的倒是樊哙而不是张良:“樊哙曰:‘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为!’于是遂去,乃令张良留谢。”
就《鸿门宴》而论“樊哙闯帐”,体现的是“忠、勇、威、壮和智”,单从这一点来看,樊哙无疑是一个布衣英雄。
如何破解现在中国世风日下,社会道德沦丧,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的危局?
从领导人做起,起模范带头作用,相关部门组织各种加强道德素质的宣传活动,如街头宣传、广播、、网络电视等。对社会上起坏作用的毒瘤们严惩,对优良风气给予表扬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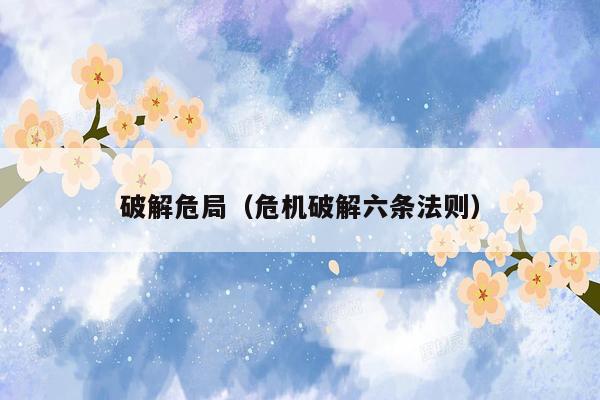
看淡生死,才能不惧生死
惧怕生死,是因为没有参透生死;看淡生死,才能够无所畏惧,直面人生。
当一个人满怀对生活的怨恨和哀叹时,生活和生命兼容的结果,就只剩下了一种味道:苦。
生是一种苦,老是一种苦,病是一种苦,死亦是一种苦。但凡把生老病死视为恒苦的人,基本上是沉沦苦海,无际无涯,几番挣扎,直至沉溺。
生命,岂只是一个苦字了得。
其实,受苦,认命,不是生命存在的本质。生命之所以能不断延续、进化,源于生命具有适应环境、克服困难、破解危局、善待自己的丰富内涵。生命就是一种全程的展示与绽放,而成长之苦恰如生命所需的各种养分,唯有经过苦难艰辛,才显出生命的壮丽与华美。生根发芽、抽枝长叶、开花结果、枯萎凋零,既是生命各阶段面临的一场场大考,更是生命成长中一次次起承转合。 当悲情诗人都在为枯枝败叶而哀婉悲叹时,他哪里知道,岩土之中的根系正在为孕育下一次绽放与盛开做着有条不紊的充分准备。
苦重愁深的人,食之无味,睡不安稳,行无动力,苦字扎心,悲悲戚戚,萎靡不振。这种恒久而巨大的负能量终其一生,如影随形,深入骨髓,害人不浅。即便是为逃脱苦海遁入空门,诵经求法而真正超脱苦海者,亦是凤毛麟角,多数人只是由一只酱缸钻进了另一只染缸,延续着别样的生苦。
但凡生命,越是苦难,越显出坚强。越是安逸,越接近灭亡。
生命进化的自然法则,就是优胜劣汰。唯有历尽寒暑,饱受风霜,千磨万击、久经考验,才能显出生命的灿烂和人文的华彩。温室花朵式安逸与舒适的人生观,势必会被现实无情碾压与强力破碎。
生死之苦,源于过分看重生死的缘故。
生命兴亡是一种自然规律。视死如归,自然终结,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应该是所有生命最原始、最直接、最朴实、最真实的一种生死观。
纠结于生死,沉湎于苦乐,乃人之常情,自古皆然。一旦超脱于生死之外,超越于生死之上,虽为君子所景仰,却难被常人所理喻。庄子鼓盆而歌,高人雅士和文人墨客赞为经典,但这种有悖常情的异象,在现实生活中很难为世俗所容,甚至为世俗所累、所毁。
是生命,就都有死亡,人也在所难免。这生生死死,来来去去,就是一种生命的常态。
把生死看的太重,生苦和死苦就犹如泰山压顶,那份沉重感有时让人窒息,往往是生得不轻松,死得不洒脱。 民间有句话叫“死不起”,这既是死人在精神和经济上对活人的终极大碾压,也是活人在良心和道德上对自己的一次大救赎。
人的生死观,看似复杂,其实也简单。
所谓的生苦,就是一种求之不得苦。也可以说是由求之不得衍生出来的一种愤愤不平的悲情。
怀才不遇,老天不公;命运多舛,苦大仇深;自信胸中有报国之志,喟叹英雄无用武之地;世态炎凉,人情淡薄;苦难多多,前程渺渺;爱恨交织,悲愤填膺;妒火炽烈,怨声沸腾...... 心中十万个为什么,个个都是怨天尤人,却唯独缺失了扪心自问:我做得怎样?我改得如何?我的进步在哪里?我的不足是什么?我要如何改变自己?我该如何突破自己?我须如何提升自己......
得过且过,苦;不思进取,苦;劳而无功,苦;怠而迷惘,苦;止步不前,苦;得不偿失,苦。这一切的苦,其实是一种心苦。应对这一份心苦,还需心药来医治。我们的心药,简言之就是阳光心态和无畏精神。
调心,是一项重要工作,也是一个漫长的历程。 首先得有打开心门的勇气和决心。阴暗潮湿、发霉腐臭,是心苦者最可怕的重疾。唯有引入光和热,强化疏与通,才能逐渐改造和改善心境。
至于死苦,基于对死亡的恐惧。
林林总总的宗教,丰富和丰满了地狱天堂说、灵魂转世说、因果报应说,给生安上了紧箍咒,为死设下了恐怖圈。尤其是行将就木之人,意志薄弱,敏感多疑,一句常言,一个梦魇,一次病痛,一个眼神,就可以将其心理防线轻易击垮,使其陷入惶惶不可终日的困局和陷阱不能自拔。
因此衍生出来的丧葬习俗,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化发展。
一种是顺其自然的天葬、水葬、海葬,从此阴阳永隔,生死两清。即便是火葬,亦是一切从简,不立石碑,不占墓地,一把大火,一捧骨灰,或随风一撒,或培入泥土,一了百了,了无痕迹。这些习俗,带有明显的区域民俗特点和地域丧葬风格,简洁明快,但很难在不同地域和不同民俗的大范围内推广。
一种是由简单化越来越趋向于复杂化、仪式化和公式化。往往一个人死了,无论穷富,后人都要耗费巨资来收埋和安葬。有钱的图个风光,没钱的挣个面子,唯有这样做了才觉得心安理得,才被认为是尽了孝心。
一场丧事下来,少则几万,多则十几万、几十万,都被陋习恶俗一一分派给了制冥币、行法事、刨棺木、贩鞭炮、做寿衣、挖土坑、刻墓碑、唱冥戏、奏哀乐、办酒席等一任操办丧事的人和群体,谁又会真正在乎活着的孝子贤孙因丧举债正惶惶不可终日的窘境和悲情呢。
很多贫苦家庭的老人,至死不进医院。拖延至临终时遗言:把我治病的钱省下来,好好的送我上路吧! 儿女一般都顺着老人的意愿,硬撑着大操大办。他们声泪俱下地哭诉: 老人苦难一生不容易,我们不能再亏待他......
一场隆重的葬礼,既渗透着大悲大痛,其实也掩盖着大逆不道。
有的人家子女不孝,虐待老人;丧心病狂,令人发指;生前尽孝,乏善可陈。可一旦可怜的人死了,却高调举丧,大张旗鼓,铺陈浪费,让邻里乡亲感慨不已:老人虽生前可怜,但走的风风光光,这笔不孝的孽债也算是不了了之啦,死而无憾啦!
在中国民俗中,白事竟也被称为喜事。 或许是去掉了一个老弱病残,甩了包袱弃了累赘?或许是孝家发丧,礼数周全,轰轰烈烈、热热闹闹,让从事婚丧嫁娶营生的一应人等喜笑颜开,利从中来?或者是新陈代谢,庆祝生命的新旧更替?
若是人丁兴旺或经济殷实之家,恰有 寿终正寝的高龄老人去世,这白事就真成了很多人眼中的大喜事。老谋深算的地仙绝对不会轻易放过这大好机会。 他会故作高深地掐算好一阵:3天期不妥、五天期不利、10天期不吉,15天后乃上上良辰,发丧又发家,大吉又大利。于是,孝家锣鼓响,主管号令强,法事多隆重,往来有排场。各行其事,有条不紊,一日三餐,宾客不断。 直至活着的子孙站得腰酸、跪得腿软、两眼红肿、满脸疲惫,折腾才最终归于沉寂。
各路“神仙”都从中赚足了钱,于是齐声夸赞:老人有福呀,子女孝顺呀,难得呀,风光啊!当然,这地仙也就名头更响——凭他一句话,开心多少人!那些既得利益的人只要有机会,就 不忘推荐和高捧这位聚众发财的吹哨大哥:真是神了!经他掐算的好日子,真准,后人都发达啦!
这种大操大办,让一些不养不孝的逆子被厚葬的世俗遮掩,湮灭了老人生不如死的人间悲剧;薄养厚葬也因此被世俗纵容与仿效,淡化了老人苦不堪言的万般隐痛;厚养厚葬虽被世俗推波助澜,但也催生了很多家庭“养不起”、“死不起”的沉重负担和巨大压力。
死不起,可否催生出厚养薄葬观念完善和发展呢?难!
厚养好理解,吃好喝好照顾好,就行。何以验之?就看老人是否是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为,老有所乐。一句话,老人开心快乐就对了。
至于薄葬,无论怎样解释,都抵不过遗老遗少及世俗各界的连连呛声:生你养你,到头来却养了个白眼狼;家财万贯却原来是个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人家借钱都要让老人一路走好,他倒好,一烧完工,一撒了事,看他以后死了有何面目去见祖宗.....
想想也不奇怪。厚养老人是一种美德,没人会在这方面去寻找攻击的软肋;可薄葬却明明白白的节省了那多钱,既让那些曾经为此大大破费过的人心里越想越不平衡,也直接或间接剥夺了亲朋戚友隆重礼送亡者最后一程的机会,更让那些经营丧葬事宜者少了财源甚至断了生计。凡此种种,不遭人诟病与怨恨才怪。
这就是常人常说的生苦和死苦,而细细想来,这样的苦都是我们自己造出来的。
看看自然界,其实很多动物都远比我们活得洒脱。
死了就没了,没了就完了,完了就结了,结了就了了。
干干净净,明明白白,简简单单,清清楚楚。
未来的世界,绝对是活人的世界。活在当下,才是第一要务。怎么活好,才是全 社会 所为。
活着的意义,一旦被重新审视、认知和全新定位,活着,就是一种精彩的绽放,而不再是一种生苦的折磨。
看淡生死,也就放下了生死;放下了生死,才能超越生死,获得精神世界的快乐与永生。
恺撒名言:我来过、我见过、我征服过
生存或死亡,这是一个原则问题。
贵为王子的哈姆雷特想了很久也一直没有想明白。在他飞身一跃后也许豁然开朗,也许万劫不复。
让我们接着好好想想。
或许,生死之间,正有一道亮光,直射而来......
毛主席诗词纸船明烛照天烧什么意思?
这句话的意思是人们焚化纸钱,点起明烛,火光明亮,照耀天空,以此来送走瘟神。
第一首诗通过对广大农村萧条凄凉情景的描写,反映了旧社会血吸虫病的猖狂肆虐和疫区广大劳动人民的悲惨遭遇;第二首诗写新社会广大劳动人民征服大自然,治山理水,同时大举填壕平沟,消灭钉螺的动人情景。
全诗虽分两首,实为一体,前一首写旧社会,后一首写新社会,起到了鲜明对比的作用,其组织又如一首词的上下片,一气呵成,并且诗句意象鲜明,含蕴深厚,耐人寻味。
扩展资料:
创作背景
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血吸虫病,在中国流行了2000多年。中共中央非常重视血吸虫病的防治工作,1953年前后就派出100多名医务人员进驻重疫区余江除灭血吸虫病,治好千余人。
1956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上强调“全党动员,全民动员,消灭血吸虫病”,并且把消灭血吸虫病写进了《农业发展纲要40条》。同年,中共中央成立了防治血吸虫病领导小组,派出大批医疗队到疫区进行血吸虫病防治工作。
工作取得明显的效果,疫区余江县人们提出了“半年准备,一年战斗,半年扫尾”的口号,发挥冲天干劲,与瘟神作战。并大力兴修水利,填平沟壑,根绝血吸虫的滋生地,仅用了两年时间,就根绝了血吸虫病。
宋仁宗无子又病得昏迷不醒,大宋危急,宰相文彦博如何破解危局呢?
作为北宋一代名臣,文彦博出将入相长达50多年,曾多次出入北宋朝廷中枢,也被世人称为贤相。文彦博为人宽宏大量、心思缜密、沉着冷静、处事果断,这些在他为官期间都得到了体现。
宋仁宗病中
至和二年(1055年)六月,宋仁宗任命文彦博为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这已是首相之职。恐怕文彦博也没有想到,半年之后,他经历了为相生涯中最严峻的一次考验。
至和三年(1056年)正月,宋仁宗在接受百官朝拜时突然发病晕倒,连日昏迷不醒。文彦博作为首相,必须挺身而出,主持朝廷大局。对于文彦博来讲,这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文彦博面临几个困难:
宋仁宗病中
1.朝廷诸多大事均由文彦博带头处理,文彦博并非权臣,一旦处理失当,日后难免留下把柄;
2.宋仁宗无子,也没立太子,此时稍有不慎,容易引起朝局动荡;
3.一旦宋仁宗病逝,权力交接的重任将落在文彦博的身上,这对于文彦博来讲,责任太大了。
文彦博为了随时掌握宋仁宗的病情,找到内侍史志聪,要求史志聪允许他和同为宰相的富弼、副相刘沆,以祈祷为由,留宿大庆殿。
此时的文彦博恐怕最希望的就是两件事:1.宋仁宗赶紧醒过来,即便是病重,至少还可以安排后事;2.朝廷千万不要出大事或乱子。不过事与愿违,还是发生了几件让文彦博吓出一身冷汗的大事。
曹皇后
一、宋仁宗在昏迷中曾当众大喊:“皇后与张茂则谋大逆”。
宋仁宗虽是昏迷中说的,但他毕竟一国之君,听到这话的人可不敢真当是胡话。张茂则是宋仁宗身边的内侍,与曹皇后自然也很熟。听到此话后,张茂则一度想上吊自杀。试想,张茂则真的自杀了,那岂不正好坐实他和曹皇后想谋逆的事实吗?皇后趁皇帝生病时造反,这事一传出来,朝廷上下难免不安。
关于曹皇后造反一事,其实是宋仁宗在病中不了解情况,误会了曹皇后。宋仁宗病重后,宰相富弼曾私下联系曹皇后,可能是询问宋仁宗万一病逝,如何扶持新帝一事,曹皇后明确表示应扶持赵忠实(宋英宗)。富弼是外臣,自然不方便当面问曹皇后,于是由张茂则在两人之间传话。估计宋仁宗有所察觉,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误以为曹皇后和张茂则想谋反。
曹皇后
那么,文彦博是怎么处理此事呢?文彦博采取了两个措施:
1.把张茂则叫来,骂张茂则:“皇上有病胡说而已,你怎么当真?你如果死了,让皇后怎么自处?”然后,文彦博对外宣称这是宋仁宗病中乱说,让群臣不要相信。
《续资治通鉴长编》:彦博召茂则责之曰:“天子有疾,谵语尔,汝何遽如是!汝若死,使中宫何所自容耶?”